“药占比”,一度被视为推动处方外流的关键力量,但在实施过程中,医院普遍采取“做小分子、做大分母”的应对措施,制度设计的缺陷被不断放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单一粗放的“药占比”制度备受责批,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药占比取消已经不是新闻,但业内人士的担心犹在。从理论上讲,药占比取消意味着医院的用药选择空间扩大,低价/值药不再是唯一选择,在“以药养医”的医疗传统作用下,处方外流的进程进一步放缓。
实则不然。国家给出的“补救措施”,是通过合理用药的指标取代药占比,“药占比”成为新政的题中之义。根据官方给出的种种线索可以推断,“合理用药”政策体系中至少包含但不限于按病种付费、总额预付制等医保支付制度的导入,利用医保杠杆限制“大处方”,是被普遍认同的做法。
与此同时,还可以看到一揽子政策可以充分发挥联动作用:
1.以“4+7带量采购”为未来导向的招采制度。官方明确,“带量采购”制度将逐渐从试点城市向全国范围推广,而“带量采购”带来的不止是药品价格的断崖式下跌,更是通过“量”的限制事实上控制医院的用药行为。
2.医保目录调整。国家明确6月底将生成2019版医保目录,从日前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来看,一则目录范围会有所扩容,二则将形成医保目录、基药目录以及采购目录间的联动,其中价格联动成为重要内容。因此可以想见,医保“保基本”的设计理念将影响医院的用药结构。
3.国家禁止医院自建药房和药房托管。斩断医和药间的利益关联,是实现医药分开、处方外流的终极力量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国家禁止医院自建药房和药房托管,实为釜底抽薪之举。
透过以上种种政策可以看到,医院的用药范围将被严格控制在具有“低价”特征的各种目录,这一方面弱化了患者的用药选择权,另一方面增强了“竞争品种”在院内市场的流通难度。笔者从最近的几次就医经历明显感觉到,医院/医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“解除”对处方的拦截,患者手持处方可以自由选择购药场所。
这样的情形或许与药店的认知存在较大差距,对大多数药店来讲,“一方难求”仍是现实困境。笔者认为,目前处方外流的难点,不是处方的“可流动性”,而是患者的“可流动性”,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值得整个行业思考的问题。
从笔者本身的感受说起,选择医院而不选择药店的原因在于:
1.惰性使然。寻医问药本就是一项“重体力”活动,尤其是到大型医院就诊,如果其间需要进行检查,至少需要耗费半天到一天的时间,那么,在院内院外药品价格相同(甚至院内价格低于院外)的情况下,实在找不出走出医院的理由。
2.屡屡碰壁。多数患者其实都有相同的经历或感受,拿着处方到药店,或多或少都会面临“品种不足”的问题。药店品种丰富的优势在处方面前荡然无存,事实上,处方药长期的双轨制发展,极大地限制了药店的供应链能力。
3.终端拦截。因为医院招采制度的改革,“弃标”或“落标”品种会大量转移到药店,这些品种往往集中在原研药品、专利药品、重疾药品等,相对医院品种在价格上具有较大差距,简单粗暴地终端拦截会影响药店的价格形象。仅从价格的维度出发,药店在处方药各品类理应重新设置销售体系以及后台的考核体系,传统OTC甚至非药品的“玩法”恐怕不灵。
以往,我们把处方流转不畅归责于医院对处方的“保护”,但通过笔者的几次就医经历发现,处方流转的重要障碍在于持有处方的患者。如何使患者“迈开腿”,是需要药店重新思考的问题,同时也应是需要政策制订者正视的问题。(中国药店)
News
相关文章

2020-10-24

2021-08-14

2021-10-09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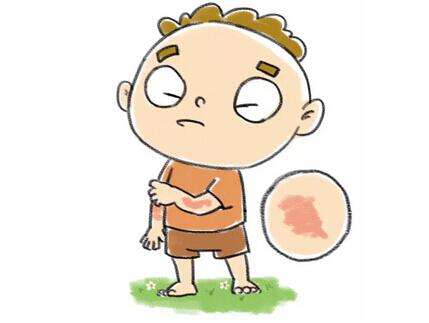
2021-06-28

2021-08-13

2023-01-17

2021-07-16

2021-02-28

2020-07-09

2020-09-02
Next
下一篇